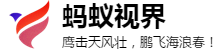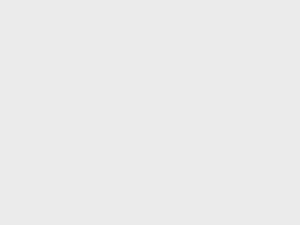- A+
石家庄不是庄,夯补市,也不是市。
石家庄在河北,人口上千万,灯红酒绿的,是国际型的大都市。而夯补市在湘西,是穷乡僻壤的苗家山寨,人口,才两百来号。
夯补市是苗寨,一座很不起眼的苗家山寨,属吉首管辖,可十有八九的吉首人,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座山寨。旧时,那些做土特产买卖的商人,他们知道,因为每年,季节来临,譬如板栗,桐油,茶油,五倍子,金银花等等,这些土特产和药材,他们都是去夯补市采购,因为夯补市量大。
夯补市在吉首北,逆峒河支流文溪河而上,大约有三十来里。整个村庄姓石,姓龙,姓秧,其中,有两家姓杨的,他们都信奉佛教。
据说,最初的夯补市,位置不在现在这个地方,在与夯补市相邻的,距离大约一千米外的“德让卡”,后来慢慢发展。鼎盛的时候,达到六十多户,曾经出现过七十“呆侧”(苗语:后生),七十“呆帕”(苗语:姑娘)一同出工的故事。说因为当时的年轻人比较多,嘻嘻哈哈地经常一起去做工,穿的又全部是草鞋,涉过村边那条小河时,常常把路面踩起一里长的湿漉漉的水印,代代相传,并且作了夸张,说是因为当时的草鞋太多,草鞋吸水性太强,把小河水都踩干了。
清嘉庆年间,有来自保靖,花垣的难民,漂泊到“德让卡”,并喜欢上了这里的山水良田,想定居下来,但因地方狭窄,容不下蜂拥而至的定居者。于是,与“德让卡”人一道,迁往现在的夯补市。
到了上世纪的五十年代,国家搞土地改革,建立农业初级社,有工作组干部进驻夯补市,说夯补市这个名字很拗口,苗音苗意,怕是影响村里将来的邮政通讯。还有,整个村庄才七十来户人家,两百来号人口,不识字的村民,还了占绝大多数,甚至,还有一些娶不上媳妇的老光棍,衣食都有问题。便依了毛主席的“自力更生,奋发图强”的词句,改了夯补市村为“自强村”。希望夯补市人在党的领导下,通过努力,彻底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状况。但倔犟的夯补市人,习惯了家乡的烂泥巴味,依然延续着“夯补市”,这个古老的名字,假如外出打工,升学考试,或报名参军,他们都喜欢拍着自己的胸脯说:我是夯补市人。
夯补市依山而建,前后左右都是大山,远看,夯补市更像以大山为主题的盆景里的村落。它的对面是阿婆山,阿婆山高大挺拔,属武陵山系,山顶有两块巨石,高低不一,酷似抱着孙宝宝的老阿婆,因此而得名。上世纪的1973年,搞全国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,村委书记龙文唱,在县委,县水电局的支持下,带着夯补市人,历时两年,在阿婆山的半山腰上,修了一条渠道,渠道长约两千四百米,在当时是一项大的工程,号称“万米渠道”,引了“九奶冲”的水,为阿婆山的肥田沃土提供了灌溉,一时成为当时吉首县农业学大寨的榜样。至今,远远看去,那条水渠仍然像飘带一样,很潇洒很飘逸地依附在阿婆山上。
背后也是山,夯补市人叫它“编鄂”,垂直高度大约一千米,而且陡峭险峻,气势磅礴。山顶的巨石,露出一副峥嵘面孔,像人,又像鬼,似笑非笑的,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亿万年前的那场惊心动魄的地质运动。巨石中,有个大山洞,洞口高约两米五,宽约一米五,洞深约两百来米。山洞里曲折婉转,黑暗,阴森恐怖,遍布着高低不一,奇形怪状的钟乳石,有乌云一样的蝙蝠群,贴在洞窟的石崖上,叽叽咕咕地看着来访者,特别使人留恋的是洞里的地气,像雾一样地从地下冒出来,来势汹汹,弥漫着整个山洞。在洞里休息玩耍,就像呆在一间天然氧吧里,轻松快乐。上世纪的七十年代,我还小,到了秋收季节,我喜欢跟着大人们,去“编鄂”附近的包谷地里收包谷,远远地,我就看到一群猴子,在山洞周围的那些野藤上,无忧无虑地荡秋千。
往北,翻过“龙江坳”,便是夯沙村,夯沙村是个乡场,属保靖县领地,因此,夯补市实际上与保靖县接壤。
夯补市实际上是树林覆盖着的村子,板栗树,枇杷树,野板栗树,松树,杉树等等,密布着夯补市。特别是板栗树,每年,到了板栗成熟的时候,刺猬一样的板栗球壳裂了口,那板栗,便叮叮当当地掉在村民的瓦房上,惊得那些小猫小狗,到处乱跑。
村头村尾都是小山包,山包上,都有着百年老树。村北的那个小山包,有一棵老枫树,高有百来米样子,枝繁叶茂的,三人合抱都抱不拢。村里的龙正堂老爷爷告诉我,在他爷爷的爷爷的时候,这棵树,已经有这么大了。村里人,把这棵树视为神树,叫它“徒几懂”,意思是攀不到顶的大树,每年春节过后,到了农历二月二,村民们都到“徒几懂”来烧香烧纸,跪地磕头,祈求树神保佑全家,身体健康,万事如意。
夯补市人喜欢武术,桐油涂漆的黑色壁板上,除了挂着一些如锄头,镰刀之类的农具之外,还挂有刀,叉,枪,棍等等,民间使用的武术器材。年轻人有了空闲时间,总是喜欢到老师傅家里玩耍,讨教一些防身健体的招法,就算的大雪的天,他们也裸着身子在自家院子里练习摔,打,擒拿。乡里,县里,市里,有了重要的庆典活动,夯补市的后生们,都会去庆典会上,作武术表演。
我那时候,最喜欢看的,就是夯补市人放木排。每年,春雨春水到来之前,夯补市人就把树木从山上砍下来,一堆一堆的,横放在河边,准备好。等到春天下雨,涨了洪水,树也就差不多全干了。这时候,夯补市人,就会从忙碌的农活中,挤出时间来,他们冒着雨,八根十根十二根的,把木条子排成一排,用野藤y好,用木钉钉紧,扎成木排。然后,撑起一根长篙,顺着滔滔洪水,吆喝一些粗话,把木排放到吉首的大田湾木材公司。
秧光福老人,1970年的时候,他已经八十六岁了。他是我见过的最后一位穿和服的人。那和服,胸前呈‘y’字形,有腰带,披一块搭一块的,是一种旧款式。他家住在夯补市的村尾,年轻的时候,到所里(吉首)给有钱人当长工。平常喜欢聊天,聊“康乾盛世”,但如果说起在所里当长工那段往事,他就来了精神:“啊!乾州萝卜保靖酒,卫城马肉天天有。所里张家呀,他屋可是家大业大啊,每年,有四十运谷子。比何家,刘家都有钱,那刘家才八运谷子,还不如李家,李家虽然谷子不多,但开得有染房,每天都有大把大把的大洋进账……”他还喜欢唱苗歌,有客人到他家里来玩,他就唱苗歌给人家听。有一回他竟对着我唱:“盘古开天又辟地,孟公最先把场开……”他告诉我,这首苗歌,是他的爷爷教他的,爷爷又是爷爷的爷爷教会的,非常重要,要我学会甚至记住了。
翻阅了一些资料,“赶场”应该是汉朝初年,陆贾和陈平两位著名的政治家,通过官府明令,开启的原始市场。而秧光福老人的苗歌,出现了另外的版本,而且承上启下,一代传给一代。里面所说的“孟公”是谁?是孟子?不得而知……
现在的夯补市,在共产党的领导下,文化,生活,交通,通讯,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公交车,私家车川流不息。村头立了石碑,上面写着“自强村”。小伙子或大姑娘们,穿得花花绿绿的,打电话与外人联系,也是:“喂,喂,喂,我是吉首市己略乡自强村的某某某,欢迎你来自强村做客,我家里有上好的酸鱼,腊肉,红辣椒……”
到夯补市村里逛了一圈,乡亲们都喜欢喊我的小名“老满”,还问我的小孩有多大了,老婆在做什么。我很喜欢他们这样喊我,一问一答的,又亲切又不落空。他们还说:“老满,上山下乡十年,你都是在我们夯补市过,怎么说,夯补市也可算是你的故乡,你要常常回来走一走,看一看啊!”。
是的,夯补市是我的故乡,走进夯补市,便是回到了故乡,走进了乡音,走进了乡愁。